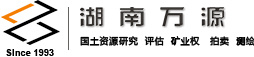資訊詳情
對接用地規劃 重塑國土空間
發布時間:
2015-05-07 12:00
來源:
作者:
《土地管理法》和《節約集約利用土地規定》等法律法規都表明,經濟社會發展對國土整治的客觀要求是編制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基本依據,也是其重要內容,土地整治規劃是建設法治國土的重要一環。土地整治規劃主要闡明土地整治戰略,確定未來五年土地整治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和目標任務,明確規劃實施的保障措施,與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耦合,是規范有序開展土地整治工作的基本依據和綱領性文件。因此,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土地整治規劃應互為補充,各有側重地共同調控經濟社會發展的“底盤”,為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起到支撐作用。
我國土地整治規劃既有實踐基礎也有國外經驗借鑒
自1998年修訂的《土地管理法》實施以來,我國已編制實施兩輪土地整治規劃,分別是2003年頒布實施的《全國土地開發整理規劃(2001~2010年)》和2012年頒布實施的《全國土地整治規劃(2011~2015年)》。而且,后者由國務院批準實施,成為國土資源領域首個進入國家國民經濟社會發展五年規劃體系的專項規劃。
經過10余年的探索實踐,全國構建形成了國家、省、市、縣四級規劃體系,發布了省、市、縣三級地方規劃編制規程或要點,明確了當前階段農田整治、市地整治、村莊整治、土地復墾、土地生態整治五大核心任務,形成了土地整治示范建設、土地整治重點區域、重大工程等多個實施抓手,創新實踐了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試點、城鄉低效土地再開發等土地整治實施機制。
“十二五”以來,湖南、浙江等8個省市陸續出臺了土地整治條例等地方性法規和政府規章,為加強和規范土地整治工作提供了強有力的法律保障。揚州市全域式規劃、上海市郊野單元規劃、北京市海淀區生態導向型規劃、嘉興市基層規劃探索等,都為全國規劃編制提供了示范和借鑒。同時,廣西龍州“小田并大塊”耕地整治模式、廣東“三舊”改造、四川郫縣村莊綜合整治、北京海淀探索規劃實施機制等實踐探索都為拓寬土地整治模式、創新規劃實施機制積累了經驗。
從國際土地整治發展的歷程和趨勢來看,土地整治成為推動農業發展、協調城鄉發展的重要動力,有完善的法律法規作為制度保障,并越來越重視促進城鄉土地格局、生態景觀建設、公眾參與機制建設、共同投入機制與產業化運作等,這也為完善我國土地整治規劃實踐提供了參考借鑒。
具體來看,國外土地整治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紀,德國、荷蘭、法國、俄羅斯等國家開展土地整治的時間較早,澳大利亞、加拿大、日本、韓國和我國臺灣地區等也都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土地整治工作。1886年德國頒布了第一部《土地整治法》,土地整治成為實施空間規劃的重要措施,空間規劃一般會編制控制性詳規和更具體的建設規劃,這種規劃體系類似于我國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土地整治規劃。荷蘭早在1924年頒布了第一個《土地整理法》,并編制了專門規劃,其后頒布的《空間設計規劃法案》明確規定了地區空間規劃與土地整治項目布局的關系。其他國家,如日本的全國國土形成規劃、韓國的國土綜合開發規劃等也都明確了土地整治的作用。
總體來看,我國土地整治規劃既有國內實踐基礎,也有國外經驗借鑒,“十三五”時期土地整治規劃應更注重科學性、實踐性和可操作性。
土地利用規劃體系需要編制實施型土地整治規劃
目前來看,我國土地利用規劃體系仍存在實施型規劃缺位、多規整合困難、目標管理偏差等三方面問題。就本質屬性而言,土地整治規劃重在從實施層面通過土地整治工程、措施,重塑利用不足或利用不當的國土空間。為此,應通過制定實施有期限的土地整治規劃,作為五年規劃體系的補充和完善。
一方面,因實施型規劃缺位,導致土地利用管理與實踐的沖突,需要五年實施期限的土地整治規劃相銜接。目前,國土資源部門主要采取“15+1”的規劃管理方式:“15”是指規劃期為15年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是各項管理的總綱;“1”是指土地利用年度計劃,依據每年經濟社會發展形勢下達2~3次用地指標,調控當年全國用地配置。然而,這種“15+1”模式缺少中間層次的實施型規劃,導致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不單要制定區域土地利用的總體戰略,還不得不具備極強的約束性和層層落實的強制性。編制內容事無巨細,空間安排落到地塊,這明顯有悖于長期規劃的特性。作為規劃的補充,每年計劃指標的調控能力有限但彈性卻很大,這使規劃越到基層越不接地氣,規劃期越臨近實施性則越差。一旦開展某項規劃中未涉及的具體工作時,首先面臨的工作就是“調規”。
這就意味著更加需要五年實施期限的土地整治規劃,銜接土地利用總體戰略,快速響應經濟社會發展,引導土地利用計劃安排,達到合理合規調整優化國土空間布局的目標。
另一方面,因土地利用規劃期限長短不一,導致在規劃編制時舍遠期求近期,需要土地整治規劃針對五年內的區域發展要求,對國土空間實施局部、可操作的調整提升。上世紀末,土地利用規劃和城市規劃的銜接、融合問題就已經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這種理論探討和實踐探索持續至今,從技術上講已經不存在太多難點,更多阻礙集中在規劃定位、任務設置和職能分工上。當前,各地正如火如荼地開展“三規”、“四規”合一工作,其邏輯是以經濟社會發展的五年規劃為指導,與15年~20年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城市總體規劃的空間布局安排相銜接,這樣的“藍圖”繪到底也就是五年。
對地方政府、管理部門而言,最“合適”的做法必然是舍遠期求近期,規劃編制中以最小成本完成上級部門下達的基本任務,空間安排上則根據后備資源情況,空間充裕則盡可能留白,緊缺則通過調規等方式規避約束,甚至不惜違法違規。為此,要實現科學融合,必須要有目標任務、規劃期限與之相匹配的實施型規劃,在戰略規劃的指導下,針對五年內的區域發展要求,對國土空間實施局部、可操作的調整提升。
此外,因理解認識上的偏差,導致土地規劃只關注指標管理,需要加強對國土空間的立體管理,以土地整治規劃重塑國土空間格局。當前,社會上對規劃形成了一種認識偏差:五年規劃管項目、土地規劃管指標、城市規劃管布局。國土資源部門作為土地資源的主管部門,是要從整體上配置各類、各行業用地,實現總體效率最優、可持續,僅對指標進行管理顯然很難達到這一目標。
特別是當前經濟發展全面進入轉型升級期,傳統農業、制造業正在進入改造升級階段,后工業化城市的發展進入內部空間的優化階段,指標、邊界的管理已經不能滿足國土空間管理的需要,要轉變方式,注重空間效率、空間服務品質的提升,加強對國土空間的立體管理。具體可包括:規劃管制、審批許可、市場調節、整治投入四大調控手段,尤其是土地整治工程、措施,通過長期、精確地改造、提升,達到重塑國土空間格局的目的。
“十三五”時期,土地整治規劃編制要有制度創新
“十三五”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定性時期,也是第三輪土地利用總體規劃頒布實施的最后一個五年實施期。新常態下科學部署“十三五”時期土地利用安排,尤其要準確定位土地整治規劃,既要順利完成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布置的主要任務,更要主動適應、調整規劃目標,在任務設置、編制程序上與各級五年規劃編制相耦合,在指導思想、制度設計上有所創新,支撐經濟社會的轉型升級。
建立完善國土規劃體系。采取“50+15+5+1”的模式,加快推進國土規劃的頒布實施,使之成為國土空間的頂層設計,指導我國未來50年~100年的國家空間戰略設計;明確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戰略定位,從中長期(15年~20年)謀劃國土空間格局;強化土地整治規劃的實施型、滾動型定位,轉變工作方式,主動銜接各級五年規劃;加強規劃實施評估,增強土地利用年度計劃管理的科學性。
科學編制土地整治規劃。加快改進完善規劃編制技術方法,突出區域資源差異性、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性不同需求,因地制宜采取適宜的規劃手段,提高決策水平。進一步明晰土地整治范疇,合理部署土地整治布局、工程,加快以空間功能為導向、優化空間格局配置、提升空間服務品質的規劃空間分析技術研究,提升規劃科學分析技術水平。
加快土地整治立法工作。我國土地整治起步晚,現行的規范幾乎都是以國家政策、規章和地方法規等形式出現,且分布零散,在概念內涵、范圍界定上也不夠清晰,導致了土地整治實踐工作中主體不明、程序混亂、權責不一等諸多問題。為此,必須加快推進國家立法機關頒布相關法律的進程,彌補現行土地整治規范效力低下的不足,以規范指導各類土地整治活動。
注重提升服務保障能力。土地整治規劃要緊扣五年實施型規劃的定位,更加注重市、縣層面的可操作性,更加注重項目落地,通過項目的空間布局、實施模式、實施標準、實施機制等來落實地方政府的發展政策,并構成行政管理的依據。內容上,更加注重國土空間功能,用生產、生活、生態多重功能以及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視角重新審視土地整治的目標和任務。手段上,更加注重公眾參與和市場化工具,科學界定政府、公眾、企業關系,提倡由政府基于公共利益、區域統籌發展、可持續發展等目標制定并實施規劃,由市場實施土地整治項目,提升規劃的服務能力。(作者單位:國土資源部土地整治中心)
轉載:中國國土資源報
土地利用總體規劃
下一頁
下一頁